《坛经》版本源流考
发布时间:2023-07-11 10:17:10作者:心经全文网吴平(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坛经》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人们不断地修订补充,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版本。纵观当今存世的《坛经》版本,真可谓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日本学者柳田圣山主编的《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一书,收集了流传于中日韩三国的十一个不同的《坛经》版本。宇井伯寿在其《禅宗史研究》一书中列举了《坛经》的不同版本近二十种。中国学者杨曾文先生在《中日的敦煌禅籍研究和敦博本{坛经)、{南宗定是非论)等文献的学术价值》一文后表列的《坛经》不同版本更是多达近三十种。《坛经》的这些版本,其正文并不一致,有些地方有很大的出入。《坛经》版本的歧异反映了各个不同时期禅宗思想对《坛经》的影响,表明《坛经》作为禅宗的“宗经”亦随着禅宗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虽然《坛经》版本繁多,但真正独立的、有代表性的只有四种: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
敦煌本是目前现存的年代最古老的本子,全名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共32字。下署“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卷末题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法一卷”。此本不分品节,文字比较质朴。因此,有人认为它很可能是当时法海记录慧能说法的实录,也称作“法海本”。也有人认为它大约是在慧能大梵寺说法记录本的基础上,加上平日的言行、临终的嘱咐等附录性资料合编而成。敦煌本《坛经》是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1923年从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书中发现的,1928年校刊后收入《大正藏》,其影印本收入《鸣沙余韵》。1943年,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先生到敦煌访查古写经,从当地名士任子宜先生收藏的写经中发现一册梵夹式蝶装本,上面抄有四种禅宗文献,其中之一便是《坛经》,约为五代或宋初的抄本。该抄本是任子宜先生1935年在敦煌千佛山的上寺发现并保存的。向达先生在1950年写了《西征小记》小文(后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对此作了介绍。该抄本现收藏于敦煌博物馆,题目和内容与敦煌本相同,但错误较少,字体工整清秀,参考研究价值超过了敦煌本。经过校勘,可以断定敦煌本和敦煌博物馆本为同一系统,同出自完成于唐代中叶的《坛经》原本。敦煌本《坛经》约12000字,文字比较质朴,不分品目,后来由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把它分为五十七节,并撰文解说。敦煌本《坛经》的发现,揭开了二十世纪禅宗典籍与禅宗史研究的序幕,引发了《坛经》研究的热潮,大大丰富了禅宗研究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书有宋刊本,今佚。《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六祖坛经》一卷,僧法海集。”(《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宋陈振孙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356页。)《郡斋读书志》著录的也可能是经过法海整理过的本子:“《六祖坛经》二卷,右唐僧慧能授禅学于弘忍,韶州剌史韦琚请说无相心地戒,门人记录,目曰《坛经》,盛行于世。”(《郡斋读书志》卷三下,第19页,宋晁公武撰,清刻本。)
为了适应禅宗思想的发展变化,后世禅宗僧人便借慧能之名,一再对《坛经》加以改编。晚唐僧人惠昕的改编本题为《六祖坛经》,分上、下两卷,共十一门,约14000字。前有惠昕序,称“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可见他做过一些增删工作。惠听本的内容虽然与敦煌本有一些出入,但基本一致。增加了慧能得法归来避难、传五分法身香、朝廷征召等事迹。“坛经传授”从法海一直传到圆会,多传了圆会一代。由此可见,惠昕所依据的底本是圆会所传的本子,与敦煌本相近。据胡适先生和钤木大拙考证,惠昕改编《坛经》当在北宋太祖乾德五年(967)五月,后有宋刊本行世,《郡斋读书志》著录:“《六祖坛经》二卷(一本作‘三卷’),右唐僧惠昕撰,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末,慧能号六祖。凡十六门。周希复有序。”(《郡斋读书志》卷三下,第17页,宋晁公武撰,清刻本。)惠昕本的刻本已失传,后在日本京都兴圣寺发现抄本,因此又称“兴圣寺本”。日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等都是它的异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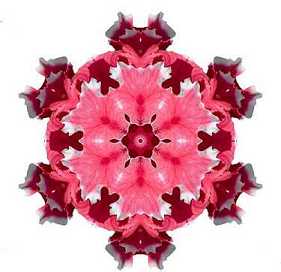
北宋至和(1054-1056)年间,僧人契嵩又将《坛经》改编,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简称《曹溪原本》,一卷,十品,约20000余字。郎简序称契嵩抛弃了原来“文字鄙俚繁杂”的旧本,改用“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可见契嵩本根据的“曹溪古本”不同于旧本。胡适先生以现存《坛经》的各种版本与敦煌本相比较,发现最早在内容上发生重大变化的就是契嵩本,其后的宗宝本只是在契嵩本的基础上添枝加叶而已。因此,关键是要考察清楚契嵩本所依据的“曹溪古本”。胡适先生最早注意到了久已在中国失传、而在日本尚有传本的《曹溪大师别传》。此书大约作于慧能死后七十年左右,即唐建中二年(781)左右。经过胡适先生的详细考证,可以确认契嵩所谓的“曹溪古本”,其实就是《曹溪大师别传》,因为契嵩本中所增加的主要内容,都可在《曹溪大师别传》中找到。甚至可以说契嵩本就是敦煌本(或惠昕本)与《曹溪大师别传》的合编本。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僧人德异在“吴中休休禅庵”刊行《坛经》,世称“德异本”。据有的学者研究,德异本很可能就是契嵩本,不过经文已不是三卷,而是一卷十门。.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前数年,光孝寺僧人宗宝再将《坛经》改编,题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十品,20000余字。宗宝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跋》中说:“明教嵩公常赞云:‘天机利者得其深,天机钝者得其浅’。诚哉言也。余初人道,有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人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此跋文写于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刊行也可能在这一年。从这篇跋文可看出宗宝在校雠时,根据三个不同的底本增加了一些文字,对《坛经》作了一些修改。此本最早有元刻本,据《文禄堂访书记》著录:“《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宋释宗宝撰,元刻本,附说法图,次题门人法海集,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四字,黑口,至正二十七年德异序。”(《文禄堂访书记》,卷三,43页,王文进撰,民国三十一年(1943)北京文禄堂铅印本。)这里的著录有两处错误,一是书名应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二是宗宝是元人,不是宋人。由于宗宝本的错误少,分为十品,品名的概括性强,文字经过润色,比其他本子流畅优美,可读性强,便成为明代以来的流行本,历代的重刊本有数十种。
就上述四种《坛经》版本而言,敦煌本最早,但它离慧能寂灭至少有七十年的历史。在敦煌本之前,《坛经》就曾有过被人“改换”的历史。南阳慧忠就曾说过:“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八,见赵晓梅等主编《中国禅宗大典》第2册,102-10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2月。)南阳慧忠卒于唐大历十年(775),他发出这些慨叹大约是在慧能逝世以后五十年左右,可能指的是南方禅宗的状况。从慧忠的慨叹可以得知:从慧能逝世(713)至慧忠逝世(775)这六十二年之间,至少已经有两个《坛经》版本在流传:一个是慧忠早年见到过的《坛经》本,另一个就是经过“南方宗旨”改换过的版本。,慧能去世后不过数十年,就有人“改换”《坛经》,后世就不用说了,多种《坛经》版本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坛经》影响广泛,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需要对它进行不断的改编。每个改编《坛经》的人,都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按某一版本作了删改调整。正因如此,这些《坛经》改编本尤其是宗宝本受到了后人的攻击和批评。
清朝初年,王起隆不能容忍宗宝的修订,对宗宝本大肆攻击:“窃谓宗宝之自用自专,大舛大错,当以佛法四谤定之。佛祖建立一切法,后人增一字为增益谤,减一字为减损谤,紊一字为戏论谤,背一字为相违谤。四谤不除,则百非俱起,退众生心,堕无间罪业,不通忏悔矣。宗宝之于《坛经》,按之四谤,实无所不有。数其大端,更窜标目,割裂文义,颠倒段络,删改文句。其胆甚狂,其目甚眯,安得再迟鸣鼓之攻哉!”(《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见《普慧大藏经》四本《坛经》合刊本。)宗宝本集各本之大成,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王起隆则对宗宝本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真是不知变通,迂腐之甚。其实与德异本相比,宗宝本并没有重大改动,实在不值得王起隆如此义愤填膺。
在现代学者中,胡适先生对《坛经》改编本批评甚力。1930年,胡适先生发表《坛经考之一》,对《曹溪大师别传》作了考证,最后得出结论;“总之,《别传》的作者是一个无学问的陋僧,他闭门虚造曹溪大师的故事,装上许多年月,俨然像一部有根据的传记了。可惜他没有最浅近的算学知识,下笔便错,处处露出作伪的痕迹。不幸契嵩上了他的当,把此《传》认作曹溪古本,采取了不少材料到《坛经》里去,遂使此书欺骗世人至九百年之久。”胡适先生对《曹溪大师别传》的思想内容,未加全面的深入考察,以至认为:“《曹溪大师别传》实在是一个无识陋僧妄作的一部伪书,其书本身毫无历史价值,而有许多荒谬的错误。”(《坛经考之一》,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中华书局,1997年12月,481-483页。)
《曹溪大师别传》虽有一些错误,但还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例如,《曹溪大师别传》记载慧能离开家乡后,先到曹溪,与村人刘志略结义为兄弟,并为无尽藏尼解释《涅椠经》。此事在敦煌本《坛经》中无记载。这表明慧能在见弘忍前有一段学佛的经历,因此对他在初见弘忍时就佛性所发表的一番见解,就不会使人感到突然了。后来契嵩本、宗宝本都采纳了这部分内容,不过都把时间移到了慧能黄梅得法回到曹溪以后。又如《曹溪大师别传》记述了慧能在广州法性寺与印宗法师论《涅椠经》义一事,虽不见于敦煌本《坛经》,却在王维的《六祖能禅师碑铭》中有所记载。法海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中也提及了“会印宗法师”一事。这两段记载均突出了《涅粱经》与佛性问题,表现的是慧能对《涅架经》的“自悟”、“自解”和对佛性“不二之义”的发挥。表面看来,这似乎与敦煌本《坛经》突出《金刚经》有所不同。(《曹溪大师别传》记载弘忍传法慧能时,是慧能与弘忍论佛性义而不是听弘忍说《金刚经》)。如果从慧能的整个思想过程来看,这正好反映了慧能思想中集般若实相说与涅架佛性义为一体的特色。)
由此可见,胡适先生对《曹溪大师别传》所下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契嵩本《坛经》取材于《曹溪大师别传》的部分内容,正好弥补了敦煌本《坛经》的不足。
1934年,胡适先生又撰《坛经考之二》,对惠听本作了考证,兼及敦煌本和契嵩本。胡适先生认为敦煌本是最古真本,惠昕本中“增添了许多很浅薄的禅宗滥调,而契嵩以后多沿用他的改本”,并批评契嵩本是“妄改”,又说:“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胆真可令人骇怪了。”(《坛经考之二》,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中华书局,1997年12月,493-494页。)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由于胡适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很高,于是就有些人附和其说,对《坛经》版本的说真道伪之风愈演愈烈。
1980年,郭朋先生出版《坛经对勘》一书,对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作了对勘,在他所作的按语之中,“窜改”、“编造”、“硬塞私货”、“以假当真、真伪不辨”、“斑斑伪迹”、“无稽之谈”、“窜改成癖”等字眼比比皆是。
1982年,郭朋先生出版了《坛经校释》。1987年,又出版了《坛经导读》。在这两书的前言中,他征引了古今中外学者有关《坛经》版本的论述,把《坛经》真伪之说发挥到了极点,最后得出结论:
时间愈晚,字数愈多。这一情况清楚表明:愈是晚出的《坛经》,就篡改愈多,就愈多私货!作为“慧能的《坛经》”(如果它不是“慧能的《坛经》”,而是“禅宗的《坛经》”,那自应另当别论)说来,就不能不说,在后三本的《坛经》里,不少的思想内容,和慧能的思想是颇不相同的,其原因,就是由于惠昕、契嵩、宗宝等人,对《坛经》进行了肆意的篡改!
忽滑谷快天在谈及三本《坛经》的不同时,也曾指出过:作为《慧能语录》的《坛经》,由于传写时文字上的改换,以致在《坛经》里存在着“玉石相混”的情况(详见《禅学思想史》上卷第十一章第二节《坛经三本之不同》)。“玉石相混”,犹言“鱼目混珠”。这一论断表明,在《坛经》(尤其是晚出的《坛经》)里,确有赝品和私货!可见,《坛经》之曾被人们所篡改,乃是一种为古今、中外学者们所公认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抹煞的。(《坛经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5月,39-41页。)
《坛经》版本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人修订补充,这是公认的事实。如果认为后出版本的修订补充是“肆意的篡改”,是“鱼目混珠”,是“私货”,那就值得商榷了。一部作品是要经过反复地修改,然后才能走向成熟,才能成为经典。《坛经》经过契嵩、宗宝等人的修改之后,慧能的禅法更为简易明白,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净慧法师在《关于慧能得法偈初探》一文中对郭朋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从慧能逝世到宗宝本《坛经》问世的578年间,《坛经》的发展演变不像中外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是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即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而是一个由繁到简,又由简复原的过程,即古本(或曹溪原本)——惠昕本(或类似之本)——敦煌本(或类似之本)——契嵩本(复原本)。净慧法师还进一步提出:
我不知道有关学者凭什么理由只肯定距慧能逝世一千二百五十多年后发现的敦煌写本《坛经》才是《坛经》的“最古”、“最初”的本子,而否定那些在慧能逝世后二百年到五百年间几次发现的《坛经》古本都是“自欺欺人”的“私货”?在地处曹溪万里之遥,时距慧能千载之后,犹能在鸣沙石室发现一本残缺不全、错字连篇的写本《坛经》。试问:在六祖禅宗风行之地,慧能真身衣钵所在之乡,惠昕、契嵩等人在六祖逝世后二、三百年中,就几次发现过内容翔实的“古本”《坛经》,这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凭什么还厚诬惠昕以下各本是“画蛇添足”“贩运私货”呢!敦煌本《坛经》既是唐末宋初之物,其中又明明写有四代相传的人名,又怎么能说是“最初”的原文呢?
然而使人迷惑不解的是,国内外研究《坛经》的学者一方面用惠昕以下各本来改正敦煌本的错字漏句——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另一方面,当惠昕以下各本与敦煌本在内容上有出入时,就认为只有敦煌本才是正确的,其他各本的内容只要是敦煌本所没有的,就都是“恣意篡改”、“贩运私货”!这种态度就有欠公正了。如果没有惠昕以下各种版本的《坛经》流传于世,我们今天要想补充敦煌写本的《坛经》的漏句错字,要想如实地了解慧能的生平和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见《法音》1982年第2期)
净慧法师的论述很有道理,自成一家之说。国内还有些学者不赞成郭朋先生的观点,这里限于篇幅,也就不一一征引了。
现存《坛经》大致由三方面内容组成:一、慧能自述生平;二、慧能开法授戒说般若禅,三、慧能与弟子们的问答。第一、二部分的内容大体上是慧能在大梵寺的开法记录,各种版本之间的出入并不是很大,基本上反映了慧能出身贫苦、黄梅得法、南归传法的生平事迹以及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禅学思想。第三部分,即慧能与弟子的问答及临终嘱咐等,后出的版本增加了不少内容,但从各种灯录中有关慧能弟子的记载来看,这部分内容基本上还是司信的。由于在大梵寺听慧能说法的弟子很多,因此,对形成的《坛经》本子各有修订补充,这是形成《坛经》版本众多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说不等于后出的版本所记载的东西就一定没有先出的版本真实。例如,慧能在广州法性寺会印宗法师,并说出了“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惊人之语,成为后人时常拈提的“非风非幡”的公案。这不见于敦煌本《坛经》而只见于以后的《坛经》各本,但在敦煌本《坛经》之前的《历代法宝记》中有此记载。任继愈先生在肯定敦煌本《坛经》的资料价值的同时还指出:“要考虑到,此后的其它版本,成书迟,其中包含的思想可以很早。”(《敦煌坛经写本序》,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这个观点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慧能的得法偈也是《坛经》版本问题中的焦点之一。得法偈是慧能思想的集中体现,对研究慧能的思想和禅宗南宗来说,这首得法偈的每一个字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敦煌本《坛经》与其它各本《坛经》恰恰在这首得法偈的字句上出现了分歧。敦煌本《坛经》中的得法偈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姓(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其它各本《坛经》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有’亦作‘惹’)尘埃!”
郭朋先生在《坛经对勘》中说:“惠昕带头,把‘佛性常清净’,窜改为‘本来无一物’。这是从思想上对惠能作了根本性的窜改:把‘佛性’论者的惠能,窜改成为虚无主义者(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字面上的窜改,因为,从思想上说来,他们并不能作到这一点),从而为以下更多、更大的窜改,作了极为恶劣的开端。而且,以后,随着契嵩、宗宝本的广泛流通,这首‘本来无一物’的窜易偈文,竟然取代了‘佛性常清净’的偈文,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人所共知的偈文。致使千百年来,以假当真,真伪不辨。这项窜改,始作俑者是惠昕,而广为流布、张大其影响者,则是契嵩和宗宝。”(《坛经对勘》,齐鲁书社,1986年6月,19页。)
郭朋先生说惠昕首先改动了慧能得法偈,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惠昕本《坛经》早十五年成书的《祖堂集》中,就有“本来无一物”的记载:“行者却请张日用:‘与我书偈,某甲有一个拙见。’其张日用与他书偈曰:身非菩提树,心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祖堂集》卷二《第三十二祖弘忍和尚》,岳麓书社,1996年6月,54页。)
在比惠昕本《坛经》早六年成书的《宗镜录》中也记载了慧能的得法偈:“如六祖偈云:菩提亦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用拂尘埃。”(《宗镜录》卷三十一,见《中华大藏经》第76册,401页,中华书局,1994年5月。)

从以上两条例证可看出,早在惠昕本《坛经》之前,“本来无一物”的说法就很流行,惠昕决不是窜改慧能得法偈的“始作俑者”。
从文气上看,“本来无一物”比“佛性常清静”更为合适。慧能的得法偈是一个整体,一气呵成,四个否定句,显得气势磅礴,不同凡响。如果第三句是“佛性常清净”而不是“本来无一物”,那么不但失去了一气呵成的气势,在内容上也平淡无味。李泽厚先生说得好:“《坛经》敦煌本与流行本相比,与其去责备后者之背离原作,似不如肯定后者正是某种发展。如‘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显然比‘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要更为彻底和明畅。”(《庄玄禅宗漫述》,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99页。)
综上所述;多种版本的《坛经》各有其价值,在使用时应当有所选择,不能盲目地肯定一种版本而否认其它三种版本。《坛经》的流传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最初是由法海记录,经手抄流行。但是听慧能说法的弟子有数十人,这就不能肯定其他弟子没有记录,更不能说他们对法海记录的《坛经》没有进行补充。敦煌本《坛经》显然就是经过神会一派弟子的整理。后出的三种《坛经》在经过加工整理后,分了品目,显得更有条理,不但基本内容与敦煌本大致相同,而且还补充了许多敦煌本所未曾收入的内容。就以宗宝本《坛经》为例,“机缘品”、“顿渐品”中主要是慧能与其弟子之间的问答,这些内容散见于各种灯录中,就史料价值说是可靠的,收入《坛经》可以集中地反映慧能的思想。因此,《坛经》多种版本的存在,应该说为研究南宗禅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